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将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
摘要:当前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已成为左右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又将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未来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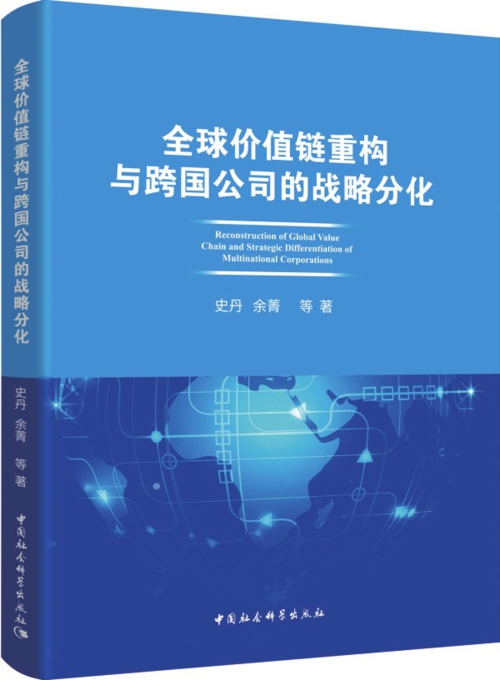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史丹 余菁 等著
史 丹
跨国公司是两轮现代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产物。在第二轮现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跨国公司群体日益走向成熟,主导和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经历了持续快速扩张,再转向小幅收缩。当前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已成为左右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又将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未来趋向。
全球化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考察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分化这一研究主题,需要将其放在全球化的图景中审视。一方面,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主体,全球价值链是跨国公司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所作的战略选择的产物,且随全球化进程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随着跨国公司对世界产出和贸易的贡献越来越大,跨国公司战略必然会对全球化、全球价值链这些变量产生更大影响。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也是影响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重要环境因素。全球价值链一旦形成后,跨国公司的战略亦受其影响。在全球化进程及全球价值链动态变化过程中,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是高度分化的,各自基于其所理解的有关全球价值链客观条件约束下的变化而作出主观决策。本书将探讨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跨国公司战略选择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与未来趋向,首先要对全球化的形势作出判断,然后才能结合中国情境来探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跨国公司战略分化现象。
如何理解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形势,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起,人类经历了全球化的黄金30年。在世纪交替之际,很多领域的研究者都在努力拥抱全球化、转向全球化。短短20年,研究风潮骤变,研究者又开始热衷于研究“全球化转向”的问题。2020年5月的《经济学人》以“再见,全球化”为封面标题,直指新冠疫情肆虐是对早已遇到麻烦的全球化又一次重要冲击。近年间,研究者从不同方面关注到了全球化在性质上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停滞,有出现逆转的可能,他将这一变化称作“全球化大潮正在转向”。如果说,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形势的表面变化,那么,全球化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本书的研究认为,全球化转向是左右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深层次因素。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考察促使全球化转向的人文社会因素,它们跳出了经济分析的掣肘,从更加广泛的社会制度、政治与文化因素来考察全球化转向,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是不充分的。本书认为,还要从生产技术因素入手来考虑全球化转向。全球化转向之所以有可能成功,必须依赖于重大生产技术创新活动的驱动,否则,仅靠人文社会因素的调节,全球化转向大概率将走向零和博弈与失败。准确认识全球化转向的形势走向,需要我们跳出各种被当前全球化逆转、衰退的表现所困扰的悲观情绪,历史地、客观地考察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发展与国际生产体系演化的历史进程,从中发现全球化转向的未来远景,进而识别出隐藏在诸多不确定性与风险因素中的可积极作为的发展机遇。
在研究中,我们亦发现,一流的跨国公司有三方面战略共同点:一是不遗余力确保对所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二是对前沿技术创新活动和对产业发展前景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技术因素保持必要的敏感;三是重视数字化转型给企业组织方式和业务形态带来的新变革。上述战略共识,值得我国企业学习借鉴。
全球化有转向两个方向的迹象和表现
全球价值链经历了从20世纪末以来的快速扩张转向过去10年间小幅收缩的演变,未来,全球化转向将带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目前,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全球化有转向两个方向的迹象和表现。
第一,是从全球化转向区域化。不少人将区域化看作全球化的替代物,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北美、欧洲和亚洲这样的重要经济区块,出现了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同步发展。例如,欧洲经济一体化,在加强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区域化特征的同时,也推动了欧洲跨国公司向欧洲之外区域的全球化扩张。因此,区域化并不是纯粹的全球化的替代解决方案,而是很有可能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区域化代表着一种去经济霸权的多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它更能够贴合世界各国在不同区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减缓经济竞争对不同地区人类群体的高度差异化的非经济价值意义的强烈冲击。在某些时代条件下,区域化的特征,可能比全球化的特征更加显性化;在另一些时代条件下,全球化的特征,又可能比区域化的特征更加显性化。因此,我们更愿意用“全球化转向”的提法,来概括当前国际生产体系出现局部区域化特征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这种局部区域化正在为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全球化酝酿新的发展动能。技术变革、环境与制度因素的变化正在推动全球价值链从分散在世界各国的分布结构,转向相对集中于区域性生产网络的方向。
第二,是从有形化转向无形化。2016年,麦肯锡发布的研究报告《数字全球化》指出,自2008年以来,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趋缓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下降,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逆转,全球化正进入一个由激增的数据和信息流定义的新阶段。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销售的制成品近1/3的价值源于品牌、外观设计和技术等无形资本。全球资本自由化配置加速推动了经济无形化和国际生产体系的数字化变革步伐。UNCTAD的百强跨国公司排名表明,过去十年,百强跨国公司中的轻资产科技型企业数量从2010年的4家快速增加为15家;同时,制造业绿地跨境投资项目金额在10年间下降了20%~25%,亚洲是唯一一个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地区,但其制造业绿地跨境投资项目金额同样出现了下降趋势。经济无形化对全球化的转向,起到间接作用和更深层次的影响。在经济无形化的前期,它与全球化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但在经济无形化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它所带来的新旧经济的分化效应会将世界割裂,形成一种典型的“双刃剑”式的局面,在源源不断产生对全球化构成巨大助力的技术与制度因素的同时,也在从技术与制度层面产生各种反全球化的因素。也就是说,经济无形化先是会加速全球化的扩张进程,然后,将推动全球化进程在多重矛盾冲突的状态下实现收缩与转向。
未来十年将是国际生产体系大转型的十年
以全球化转向的思路来审视当下的国际生产体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分析结论。首先,在世界政治经济的现存状态下,旧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能够实现的全球贸易及国际生产体系的增长潜力基本耗尽了。由于无形资本的流动往往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因此各国难以再用税收手段对财富分配重新进行调节。无形经济下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某些文化特性可能有助于解释导致很多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抬头的社会经济矛盾。
其次,当前全球化困境的性质决定了,各种为解决上一轮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与问题的治理机制的局部优化与调整不足以支撑当今世界走出全球化的新困境。这些对策措施初衷可能向好,却大有可能造成加剧全球化进程中的对抗与分裂势力的意外后果。简言之,实施全球化治理的变革,不能主要依靠于对世界人民共同福祉的善意,而需要有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方参与主体提出更加适应于全球化转向的新形势变化的应对举措。
最后,全球化的转向之门已然开启,但究竟会转向什么样的实际状态,这仍然将取决于技术与制度两方面因素的变化。正如《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的,据其对国际生产体系与跨国公司持续30年的研究经验来看,国际生产体系正处在十字路口——先是经历了20年的快速增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出现了停滞下滑迹象,又经过了2010年以来10年的暴风雨前的宁静。进入2020年后,新冠疫情对国际生产体系构成了最大挑战,从2020起至2030年的这10年,将是国际生产体系大转型的10年。
综上所述,未来10~15年将会是国际生产体系大转型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一段重要时期。面对充斥不确定性和不再平坦的全球市场,跨国公司通过差异化的战略加以应对,这是全球化转向带给各国跨国公司的必然选择。无论是在地域布局上转向区域化,还是在产业布局上转向无形化,在全球化转向给全球市场体系运行和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的形势下,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失败的风险将趋于上升。在应对全球市场环境变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的战略分化还意味着,领先者和滞后者在适应全球化转向上的绩效差距,难免进一步扩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摘编自《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分化》一书)
责任编辑:张晶